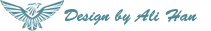(11月)“恐怖的梦魅”与《一九八四》
| 前晚,看完了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这本书把我这几年在成长过程中的许多零碎的认识贯穿起来加以深化强大,大概到零晨一点多,感觉得着内心极其的压抑,让人难以呼吸,许多乱七八糟的想法蜂拥而至。
后来我便沉沉睡去。入醒的过程中,却做起了一个奇怪的梦。在哪个梦境里,我发现自己身在一个周围堆满垃圾的角落里,四周污水横流,没有容脚的地方。哪时我还意识得着,我是一个极爱整洁的人,但我发现我的鞋不见了,又或者说刚开始一进入梦境我就 有什么东西在内心指引我,我极其小心的走到某一个角落里去,哪是一个形如在半山中挖一个地洞一样的地方,里面有不见尽头的黑。而在洞的里面一直深深地倾斜进去到无尽的里面,在下面是一潭深不见底的黑乎乎的污水,一动不动地在洞里面,污水却已经盈到了洞的边缘处。 傍晚的冷风在洞口外面还微微地泛着阴暗的日光。哪些时候,我似乎没有了呼吸,当我光着双脚走到洞口的时候,内心充满着形如恐惧般的排斥,但我为什么要到哪里去,当时我却不知道。 突然间,我发现母亲在洞边煮饭,就在污水的上面。哪里有灶吗,当时却没看见,只见着污水黑黑的在地上泛滥着沟沟壑壑。 我便对母亲说,妈我来帮你吧。于是我便用哪锅来炒菜。我却找不到油,只用一个铲在上面炒着。突然间我发现,锅里全是黑黑的污水在回旋,把菜浸得不见踪影。我的心似乎被什么东西嵌制住了,似乎有个什么东西依附在身上,一种极其无奈而又压抑的感觉。我赶紧想把污水倒掉却总发现不断不断地涌进来,而且你不知道它从哪里来。 这时我又想起大雨刚过,哪种污水泛滥的景象又成为一个景象在梦境中,而我刚才又似乎把它忘掉了;这时,洞里的哪个形如有深渊一般无限无限深的污水潭,下面满着黑透透的污水,又成为一个景象在梦境中,而我刚才又似乎把它忘掉了。我突然间感觉得着下面有一只巨兽在我向移动,而且已经在看不见的水底移到我的身旁了,于是一种极大的恐惧侵袭全身。 污水把原本亮青青的菜浸得发黑。而且,我的双手满是黑黑的油污。当时,我从来没有感受得着如此如此的压抑。我炒着炒着,我实在忍受不了了,我便说,妈,这些菜不要了,太脏了,于是我便把哪菜倒进污水里去。哪时的天,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因为我看不到太阳。 后来,突然间我听到有人在不远处叫我,我出来外面的地洞一看,原来是已经有十年不见的老同学,似乎还不止一个,有一个在不远哪边看着我,哪还真是我的老同学。有几个在一头要走过来,又有几个在向远方走去。 这些人不是早不见了吗,怎么突然间在这里?我惊疑地想。突然间我发现它们已经长得很大很大了,似乎还有一些老了的面容,但是又能让你一下子认出当年的它来。它们都是骑着自行车的,自行车的后架上装满东西,似乎有红红的桶,有大张的棉被还有卷着的席子等等,整车都是。 于是我便惊奇地问,你们要干什么去啊?有一个老同学对我说,你还不知道吗,我们的学校要举行隆重的典礼。于是我想,举行典礼,干嘛都拿这个,但我的嘴上又不问这些问题,我似乎一下子明白什么地想,我不是已经知道要举行典礼?我知道?我突然间似乎又不记得了。总之我既惊奇又疑惑。 突然间我到了一个很大的很光很亮的门口,但是哪里却又似乎没有什么人,却又似乎有很多熟悉的人在进进出出。它们都到哪个地方去的。到哪个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地方却又似乎知道是什么地方的地方。 大概,这时候便什么景象都消失了,我便一直睡,睡到第二天。 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压抑?恐惧?不解?怀疑?忘却还是其它?我却不太清楚,总之整一个梦境让你充满着如同掉进深渊的恐惧又如同在大白天下面看不到任何事情的来龙去脉,而你却不知来自何处,今天在一个什么样的世界里面。 醒来后,我慢慢想一些东西,却发现,这个梦境里的哪种感觉与东西,似乎既有《悲惨世界》里的冉阿让,又有《罪与罚》里的拉斯柯尔尼科夫,而笼罩整个梦境的感觉,尽是《一九八四》。 2011-11-17毕于广东湛江
节选: …… …… …… 他见过她;他甚至跟她说过话,这样做早没有危险。他本能地清楚,如今他的所作所为,他们几乎毫无兴趣。要是他们两个都愿意,他都能再安排跟她见一次。其实他们那次见面挺偶然。那是个三月天,在公园里。那天冷极了,也坏极了,土地坚硬,草木凋败,惟有点点藏红花冒了头,也给寒风撕得七零八落。他冻手冻脚地急着赶路,眼睛冷得流眼泪。这当儿,他见她就在十米开外走过来。他吓了一跳,见她变了样子,可说不清变了什么。他们几乎漠然地擦身走过去,他便回转身来跟着她,不过动作并不热切。他明知道没危险,谁也不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她一言不发,斜向穿过草地,像是打算摆脱他,见甩不开,便听任他走到身边来。他们正走到一簇灌木丛间,那树丛枝条光秃,破败凋残,挡不住人,也遮不住风。他们便停下了脚步。天冷得要命,寒风在树枝间呼啸,抽打着脏兮兮的藏红花。他伸手搂住了她的腰。 这里没有电幕,可一准藏着窃听器。况且,人人都看得见他们呀。可这没关系,什么都没关系。他的肌肉也骇得绷绷硬。他把胳膊搂着她,她却一点反应也没有,甚至都没想挣开他。现在他看出来她哪里变了样:她的脸色变得一片灰黄,一条长长的伤疤,从前额直伸到太阳穴,给头发盖住了一点。然而,这还算不上变化。她的腰身比以前粗实,而且叫人吃惊的是,也比以前僵硬。他记得有一次,炸了一颗火箭弹,他帮人从废墟里拽了具尸体出来。令他吃惊的,倒不是那尸体沉得要命,而是它那种僵硬难抓,仿佛抬的不是肉,而是块石头。她的身体,他觉得也是这样。恐怕她的皮肤,也不像从前那样细嫩啦。 他没打算吻她,他们也没说话。他们转身往回走,穿过草地,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看他。那仅仅是短短的一瞥,充满了轻蔑和厌恶,也闹不清这厌恶纯粹由于过去的经历,还是也加上他肿胀的面孔,以及风吹得他满眼流泪的缘故。他们并着肩,在两把长椅上坐下来,可没有挨在一起。他见她好像要说话。她把自己笨重的鞋子挪了一点点,成心踩断了一根小树枝。连她的脚,仿佛也比以前长宽啦。 “我背叛了你,“她毫不掩饰地说。 “我背叛了你,“他说。 她又很快朝他厌恶地一瞥。 “有时候,“她说,“他们拿什么东西威胁你–那东西你根本经不起,想都不敢想。你就会说,‘别冲我,冲旁人去,冲谁谁去。‘事后你可以装模作样,说这不过是在玩花招,这么说不过是叫他们快住手,不真是这意思。可是,才不是这样。那会儿你就是这意思。你觉得没有别的办法能救你,就真的打算用这办法救自己。你真想这事冲别人。他们受什么罪,你他娘才不管。只剩关心你自己啦。“ “只剩关心你自己啦,“他重复道。 “再往后,你对旁人的感情再不一样啦。“ “是呀,“他说,“感情再不一样啦。“ 好像再没什么话可以说。寒风把他们单薄的工作服,吹得紧贴在身上。坐着不说话未免太尴尬,这样一动不动也太冷。她说要去赶地铁,就站起来要走。 “我们再见罢,“他说。 “唔,“她说,“我们再见罢。“ 他隔开半步远,迟迟疑疑跟了她一段。他们再没有说什么。她没有真打算甩开他,可是走得飞快,害得他没法跟她并肩走。他本想就送她去到地铁站,可是突然间,又觉得这样冷飕飕地送下去,就没什么意思,他也受不了。他一心只想不如离开朱莉亚,回到栗树咖啡馆,那地方从来没像现在这般吸引他。他依依想着他角落里的桌子,还有那报纸、棋盘,跟满杯满盏的杜松子酒。关键是,那里准保很暖和呀。于是接下来,不全是出于偶然,他听任一小群人把他跟朱莉亚分隔了开来。他半心半意打算追上去,又放慢脚步,掉转身来往回走。走出五十米,他才又回头看一眼。大街上人不多,可已经认不出哪个人是她。十几个人急匆匆地往前赶,她可能是其中的任一个。或许她的身体又胖又僵硬,从后面压根儿就认不出来啦。 她刚才说,“那会儿你就是这意思。“他也就是这意思。不光说了,他也真盼着这样。他盼着把她,而不是他,送去喂…… 电幕上播放的音乐变了调儿。这回的腔调沙哑又讥嘲,正是那种黄色小调。而后,一个声音唱了起来–或许也没有谁真在唱,只是他记起了这样的声音: “这栗树荫荫影迷离, 你卖了我,我也卖了你……“ 他眼里不禁涌出了泪水。一个服务员从身边经过,见他的酒杯已经喝空,便再把酒瓶拿了回来。 他端起酒杯闻了闻。这东西一口口喝下去,感觉没好起来,倒是越发骇人。然而这成了他沉耽的尤物。这是他的生命,他的死亡,他的复活。每晚他靠杜松子酒晕得昏天黑地,到早晨,他又靠杜松子酒扎挣起来。他难得在十一点以前醒转来,眼皮发粘,嘴巴发干,脊背折断也似地疼;要不是前晚把酒瓶和茶杯放在床边,他一准爬不起来。中午那几小时,他便呆呆地坐着听电幕,面前放着酒瓶子。到十五点,他照例要去栗树咖啡馆,直耽到关门才回家。再没人管他干什么,再没有哨声惊扰他,再没有电幕责备他。有时候,每星期该有个一两次罢,他要去真理部,那里有间灰头土脸的办公室,早给人忘在了脑后,他要在这里做点子小工作,全是些名义上的工作。为解决十一版新话词典编纂过程中出现的次要问题,设置了不计其数的委员会;其中的一个委员会,它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下设的小组委员会,他便给任命了进去。他们正忙着草拟份东西,叫什么中期报告,可报告的是什么玩意儿,他却从来没有闹清过–好像是什么逗号该放在括号内,还是括号外的问题。委员会还有四个人,全跟他半斤八两。今天他们刚开上会就散会,老老实实表示,根本就没事可以做。到明天,他们坐下来,工作又来了劲头儿,事无巨细做记录,没完没了写呈文–那便是他们装模作样讨论的东西,变得极尽复杂深奥,于是混搅定义,离题千里,争吵辩论–甚至威胁着报告领导。可猛然间,他们全泄了气,便围坐在桌前,懵懵懂懂大眼瞪小眼,有如单等雄鸡一唱,便销声匿迹的鬼魂。 电幕一时间静了下来,温斯顿抬起脑袋。公报!哦不是,只是要换首曲子。仿佛在他的眼前,就是幅非洲地图,军队的调动便是幅图表:一个黑箭头径直开向南,一个白箭头却横向冲向东,斩断那黑箭头的尾巴。他抬头看看海报上那冷静的面孔,像是要打消心里的疑虑。怎能设想,那第二个箭头根本不存在? 他又失却了兴趣。他喝口杜松子酒,捡起白马试着走一步。将!不过这步显然不对,因为…… 他的心里,没来由想起一件事。仿佛一间屋子,给烛光照亮,一张大床铺着白床罩。他也就十来岁,坐在地板上,摇着一个骰子盒,一面开怀大笑。妈妈坐在对面也在笑。 这准在她失踪之前一个月左右。那算是暂时的和解,他忘了没完没了的肚饿,一时间孩提的爱心也开始甦醒。他清楚记得那一天,大雨倾盆,雨水在玻璃窗上滚滚流下来,屋里太暗,看不了书,两个孩子在黑暗狭仄的卧室里穷极无聊,简直受不住啦。温斯顿开始哭哭啼啼,唠唠叨叨,吵着闹着要吃的,翻箱倒柜,横拉竖拽,擂墙擂得山响,把邻居烦得直敲墙。他的小妹,只是一阵阵地嚎哭。最后,妈就说,“乖乖的,给你买玩具!好玩极啦–你准保喜欢!“她便顶着雨出去,到附近一家小百货店,那样的小店,当时偶而还能开开的。等妈回来,她带给他一个硬纸盒,盒里装了副运动棋。他还记得那硬纸板潮乎乎的味儿。真是个破玩意儿!盒子破破糟糟,木头小骰子粗糙得很,站也站不住。温斯顿绷着脸看一眼,打不起兴趣。可妈妈点了根蜡烛,他们就坐在地板上面玩起来。没一会儿,见棋子儿就要走到终点,却又退了回去,险些儿退到了起点,温斯顿兴奋得大笑大嚷。他们玩了八局,每人都赢了四局。小妹太小了,看不懂他们玩什么;她靠着枕头坐着,见他们俩笑,便也跟着笑。那个下午,他们快活极啦,就像他还是婴孩那时一个样。 他把这画面从脑海当中推出去。这记忆是假的。有时这种假记忆,便来捣他的乱。只消识破了它们,就成不了气候。有些事情发生过,有些却根本没有过。他又想起了棋盘,便重新捡起了白马–可就在这时,那只马啪地落在棋盘上。他悚然一惊,仿佛被针扎了一下。 一阵喇叭声划破了空气。这是公报啦!胜利啦!新闻之前吹喇叭,照例预示着胜利。咖啡馆里倏地一振,仿佛通上了电流。连服务员也吓了一跳,忙竖起耳朵来。 喇叭声引起了一片喧哗。电幕上激动的声音已经急急响起来;那播音员刚开始广播,便给屋外兴奋的欢呼淹没个干净。消息像施了魔法,在街上不胫而走。从电幕上,他只能听见,一切都按他预期的那样发生啦–一支舰队秘密集结起来,突然向敌人的后方出击,白箭头斩断了黑箭头的尾巴。喧嚣间,他只能只言片语听到兴奋的宣布:“伟大的战略部署……完善的配合……彻底的混乱……俘敌五十万……完全丧失了斗志……控制了整个非洲……战争结束指日可待……胜利……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胜利,胜利,胜利!“ 温斯顿的脚在桌下拼命乱动。他没有起身;可在心里,他却在跑,飞快地跑,跟外边的群众一起,欢喜欲狂,大喊大叫。他再抬起头,看一眼老大哥的画像。这凌驾世界之上的巨人!这把亚洲的乌合之众撞得头破血流的砥柱!就在十分钟以前–是呀,只有十分钟呀–他想着前线的消息是胜利还是失败,那会儿他还兀自狐疑哩。嘿,灭亡的可不只一支欧亚国的军队!打从进了爱护部,他已经变了不少;然而最后那必需的变化,真叫他革心洗面的变化,直到今天才终于完成。 电幕上的声音,还在滔滔不绝讲着屠杀、俘虏、缴获的丰功伟绩,外面的欢呼声倒已经减弱了不少。服务员也回去,干他们自己的事儿,有一个拿来了酒瓶子。那温斯顿坐在桌前如醉如痴,就没注意他的杯又给倒满了酒。他回到爱护部,人家饶了他的一切,他的灵魂雪雪白。他上了被告席,一切事全坦白,一切人全牵扯。他走在白瓷走廊上,仿佛沐浴着阳光,一个荷枪实弹的警卫跟在后面。渴望已久的子弹射进了脑袋。 他凝视着那张硕大的脸。整整四十年呀,他才算弄清楚,那黑胡髭后面藏着怎样的微笑。哦残酷的误会,徒劳的误会!哦这慈爱的胸怀,他竟然冥顽不灵地逃开去!他的鼻子两边,流下来带酒气的泪水。可是全好啦,一切都好啦,战斗结束啦。他战胜了自己。他可真爱老大哥呀!
《一九八四》简介: 《一九八四》(英文:Nineteen Eighty-Four)是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的一部政治讽刺小说,初版于1949年,与1932年英国赫胥黎著作的《美丽新世界》,以及俄国尤金·扎米亚金的《我们》並称反乌托邦的三部代表作,通常也被认为是硬科幻文学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奥威尔深刻分析了极权主义社会,并且刻划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的,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未来社会,通过对这个社会中一个普通人生活的细致刻画,投射出了现实生活中极权主义的本质。 《一九八四》已经被翻译成至少62种语言,而它对英语本身亦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一九八四》曾在某些时期内被视为危险和具有煽动性的,并因此被许多国家(不单是有时被视为采取“极权主义”的国家)列为禁书。本书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1923年至今最好的100本英文小说之一,此外还在1984年改编成电影上映。 乔治奥威尔在1948年写作《1984》之前,在英国是一个贫病交迫、没有多大名气的作家。《1984》虽在他1950年患肺病去世前不久出版,但他已看不到它后来在文坛引起的轰动为他带来的荣誉了:不仅是作为一个独具风格的小说家,而且是作为一个颇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预言家。从此他的名字在英语文学史上占有了重要的独特地位,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收进了权威的英语词典,甚至由他的姓衍生了一个形容词“奥威尔式”,不断地出现在报道国际新闻的记者的笔下,这在其他作家身上是很罕见的,如果不是绝无仅有的话。 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1984》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1983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1984》,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1984》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但是无论信奉社会主义或者反对极权主义,奥威尔都是在他生涯较晚的时候才走到这一步的。 |
十一月 17, 2011 星期四 at 9:04 下午
 是光着脚的。哪时我却不去找鞋,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做。
是光着脚的。哪时我却不去找鞋,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做。